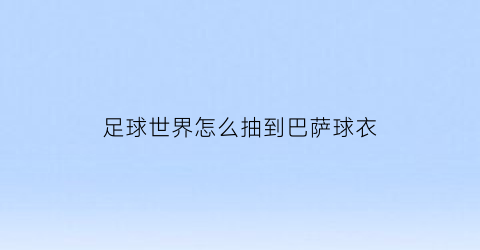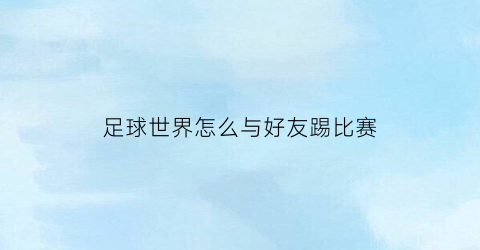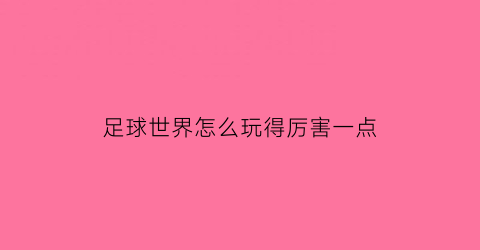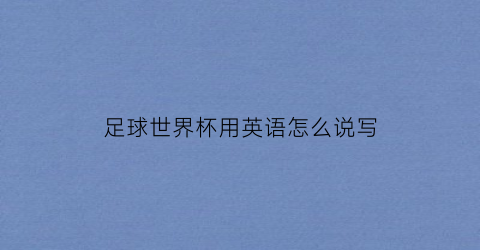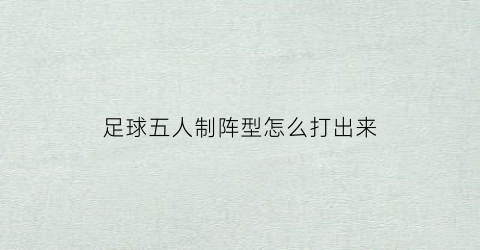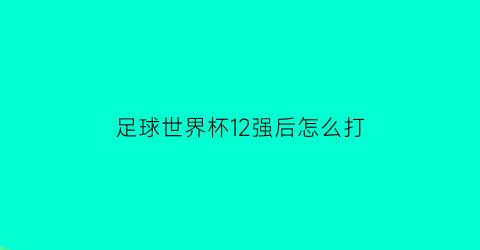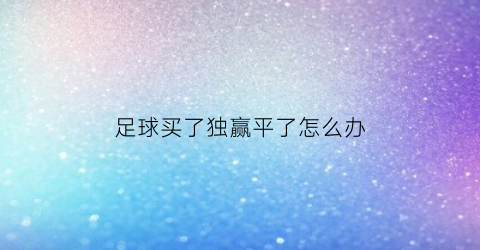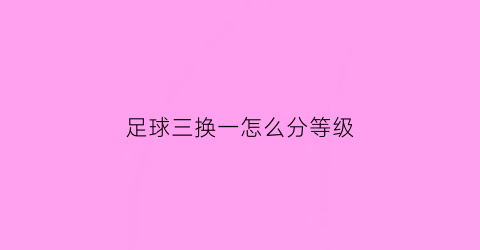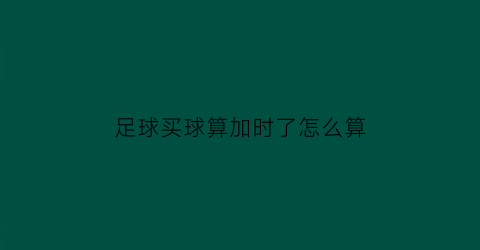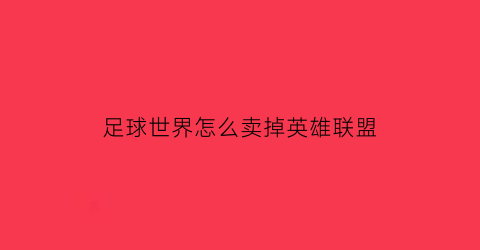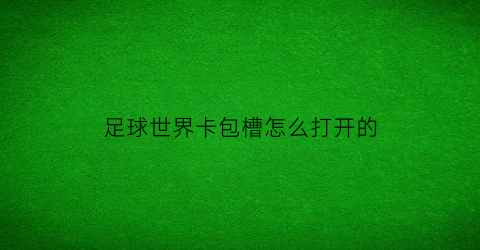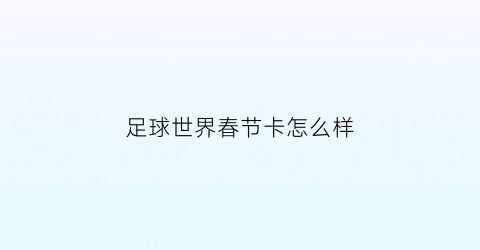阿努什·达斯特吉尔 (Anoush Dastgir) 可能是足球界最勤奋的人,但到了周六,他的工作已经付出了代价。
阿富汗男子国家队教练达斯特吉尔坐在酒店的空餐厅里,他和他的球队正在那里准备对阵印度尼西亚的表演赛。现在是晚上 11 点,Dastgir 正在与听起来像是重感冒的东西作斗争。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现在有十多份工作要做。
执教一支国家足球队在任何地方都足够艰难,但执教阿富汗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一个内战和塔利班统治的地方,曾让国家队近二十年来无法参加比赛。这个国家被认为非常不安全,事实上,足球的全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长期以来一直禁止其球队在国内比赛。大多数时候,这无关紧要:阿富汗在世界上排名第 152 位。而且它从未有资格参加重大比赛。
尽管如此,夏季情况变得更加艰难,当塔利班席卷喀布尔时,阿富汗政府垮台,其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更不用说他的成千上万的同胞——逃离了这个国家。
Dastgir 在混乱中失去了与他的部分团队和一半员工的联系。两名工作人员现在在卡塔尔的难民营。另外两人在阿富汗,急于离开。他的名单上几乎全是阿富汗难民或难民的儿子,他们多年来在荷兰、德国、美国、瑞典等地避难,逃离自 1980 年代以来困扰阿富汗的各种冲突。但仍有一些人在阿富汗度过了一段时间,今年甚至这样做也成为一个问题。
Dastgir 最重要的球员之一,Noor Husin,他六岁时前往英国,7 月塔利班逼近时,他在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 (Mazar-i-Sharif)。“说实话,我很害怕,”他说。“因为每天都有新闻,他们越来越近,他们在城郊。我在想,肯定不是。你只是没想到它会发生。”
Husin 设法到达喀布尔并争先恐后地离开了这个国家,但他 - 和他的许多队友一样 - 认为国家队已经结束了。“每个人都认为,这是结束,一切都结束了,”他说。
不过,他说,达斯特吉尔决心让它继续存在下去,让它继续服务,作为一个罕见的统一象征,在一个经常因种族或语言而分裂的国家。因此,几周前,他拿起电话安排了一场友谊赛——这是塔利班接管以来的第一场——对阵印度尼西亚。那是容易的部分。然后,他必须找到比赛场地,为球员安排航班和签证,并为每个人提供冠状病毒检测。由于阿富汗足协的银行账户被冻结,Dastgir 成功地向国际足联申请帮助资助这次旅行。
没有装备人员,Dastgir 还不得不自己运送 450 磅的训练装备,然后说服他的姐夫帮他洗。他购买了足球,安排了裁判,并且——没有通讯团队——在他的私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宣传这项比赛。他甚至与转播合同进行了谈判,以确保返回阿富汗的最多人数可以观看比赛。然后,在完成所有这些之后,他仍然需要抽出时间来执教球队。
但随着周六午夜在酒店餐厅的临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球队将悬挂哪面旗帜?
年轻的领袖
31 岁的 Dastgir 是世界足坛最年轻的教练之一。他出生在喀布尔,1989 年苏联军队离开阿富汗后不久就与家人一起逃离了该国的内战。他只有几个月大,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长大,然后定居荷兰。
在欧洲,他学习了荷兰语,并被领先的俱乐部 NEC Nijmegen 发掘。他最终被征召为阿富汗国家队,但在膝伤结束他的职业生涯之前,他只参加了几场比赛。
“我的教练说,'你必须开始执教',因为作为一名球员,我是球队的领袖,”他说。他第一次有机会带领阿富汗队出现在 2016 年,当时一名外国教练因合同纠纷而没有参加比赛。
“球员们说,'我认为 Anoush 可以处理它,'”Dastgir 回忆道。他输掉了那场比赛,但球队打得很好。2018 年,该职位下一次公开时,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那时,他正在寻找阿富汗球员。许多人是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广大阿富汗侨民、难民和他们的孩子中发现的。当 2018 年在喀布尔安排与巴勒斯坦的比赛时,这是多年来在阿富汗举行的第一场国际比赛,达斯特吉尔提出了他的许多发现。
“我想让这些球员在阿富汗感受这个国家,看到那里的人,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生在国外,”他说。“所以如果你告诉他们为你的国家踢球,他们会说,'那是什么?'”
即使是现在,该团队作为一个可见的多元文化机构的地位也出现在培训课程中。
指令是用荷兰语和普什图语大声喊出来的。鼓励以德语、达里语和英语提供。有时,Dastgir 会在句子中间切换语言。“我的第一任船长是塔吉克人,”他说。“我的第二任队长是普什图人。我的第三任队长是哈扎拉。”他的两个球员,亚当和大卫纳吉姆兄弟,出生在新泽西州。

尽管如此,随着比赛的临近,国旗和国歌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决定。塔利班的白旗,上面印有穆斯林的信仰宣言——Shahada,取代了阿富汗总统府上空的绿、红、黑三色旗。随着塔利班对音乐实行广泛禁令,国歌实际上已被取缔。
Dastgir 知道玩它并悬挂旧旗帜会引起争议;该国男子板球队在Twenty20 世界杯上遭到塔利班领导人的斥责。他知道他的选择可能会让他失去工作或更糟。
“我不怕被解雇,”Dastgir 说。“我是拥有 3700 万阿富汗人的国家队的主教练。我不是塔利班政权或加尼政权的国家队教练。我们从来没有为政府做过这件事。我们为人民做到了。”
远离家乡的干杯
阿富汗营地中没有人确定是否有任何支持者真的会来安塔利亚附近的海滨小镇贝莱克观看他们的比赛。
当 Dastgir 同意自掏腰包支付安保费用时,体育场官员对冠状病毒限制的担忧得到了缓解。还有一个问题是土耳其警察是否可能具有威慑力。近年来,至少有 300,000 名阿富汗难民和移民在土耳其找到了庇护所,其中许多人没有证件。但随着天色渐暗,开球临近,数百名球迷在体育场大门外排起了长队。
“我想表明我是阿富汗人,”穆萨尔说,她是一名 18 岁的学生,裹着一面巨大的阿富汗国旗,但非常谨慎,拒绝透露她的姓氏。四年前,她的父亲在阿富汗遇害后,她逃到了土耳其,自从她到达以来,几乎没有机会挥舞阿富汗国旗。“这是我们的旗帜。你没有另一个标志。就这面旗帜,谁也改变不了。”
六百名支持者——与体育场官员商定的限额——很快涌入,挤满了体育场一个长长的看台。
开球前几分钟,球队在中场排好队。在他们面前,阿富汗的两名替补队员展开了一面绿色、红色和黑色的大旗,那面是达斯特吉尔随身带到贝莱克的。国歌响起,一瞬间让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回到家中。没有人在那里拍摄传统的赛前照片:球队的官方摄影师几个月前逃到了葡萄牙。
这场比赛很疯狂,阿富汗球迷不断发出嘈杂的声音。一身黑衣的达斯吉尔冷静地给出了战术指示。下半场后期,他召唤了奥米德·波帕尔扎伊,这位荷兰籍中场球员最后一次出现在波兰第四梯队。第85分钟,波帕尔扎伊替补上场几分钟后,波帕尔扎伊破门得分。几分钟后,终场哨响了。阿富汗赢了,球迷们欢呼雀跃。
一名球迷跳下 12 英尺,跳到场地周围的跑道上想要自拍,但他被警察拦截并用青蛙的脖子向后退。一名名叫 Norlla Amiri 的球员爬到了队友的肩膀上,以便将他年幼的儿子传给他。
其他球迷把手机扔给球员,要求自拍。许多人想要与 Faysal Shayesteh 合影,他是一名 30 岁的中场球员,自孩提时代移居荷兰以来,他的职业生涯一直遍布全球。
几乎所有的阿富汗球迷都因为他的纹身而认识 Shayesteh,包括他胸前的纹身,展示了一架战斗机和一架攻击直升机下方的喀布尔天际线,每架战斗机和一架攻击直升机都用红心轰炸这座城市。在他的左胸上方有两个 GPS 坐标:第一个是 Hengelo,他在荷兰东部长大的城市。另一个是喀布尔,他的出生地。
“如果我谈论它,我会情绪激动,”他忍住眼泪说。“因为我知道阿富汗人民正在经历什么。我知道这是唯一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为国家队赢得一场比赛。这是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很高兴。”
Dastgir 看着这一切从后面展开,在他的手机上拍摄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发布到他的 Instagram 帐户上。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来让这一刻发生。